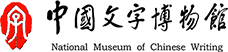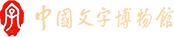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
殷墟甲骨的发现,迄今已达一百年了。甲骨确切地说是在哪一年发现的,学术界颇有争议〔1〕,今后还可能讨论下去, 但考虑到“村农收落花生,偶于土中检之”, 于是为古董商人所得之说, 其始出或在1898年冬,而由王懿荣鉴定则是1899年。不管怎样,现在开始纪念这件学术史上的大事,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甲骨的出现导致一门学科的产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甲骨学。“甲骨学”这个词系何人何时首创,有待考证,然据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率先以“甲骨学”揭橥于论著标题的,是朱芳圃先生。朱氏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的弟子,他在1933年出版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印行《甲骨学商史编》。同时,1934年《中法大学月刊》有李星可《甲骨学目录并序》,1935年复旦大学《文学期刊》有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2〕, 此后“甲骨学”作为学科名称便广泛流行〔3〕。
甲骨学的内涵可有狭义与广义。狭义的甲骨学特指甲骨及其文字本身的研究,广义的则举凡以甲骨文为材料论述历史文化者皆得纳入。过去如董作宾先生《甲骨学五十年》(后修改为《甲骨学六十年》),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严一萍《甲骨学》等,取义均较专门。本文所述也想以狭义的甲骨学为限,略陈拙见,请方家指教。
让我们先由甲骨的搜集著录谈起。殷墟甲骨到如今一共出土了多少片,因为“片”的定义不很明确,加之收藏分散,不断流动转手,要精密统计是很不容易的。5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曾估计为10万片〔4〕。近年,胡厚宣先生计算有16万多片〔5〕。最近有学者表示不同意, 仍认为“近10万片”为妥〔6〕。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 陈梦家文以小屯YH127坑情形为准,推断相当“完整的甲和胛骨数千”,不过YH127龟甲基本完好,从历年发掘经验看,实在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甲骨在埋藏时业已残碎,所以碎片所代表的完整甲骨数量会更多。
甲骨的著录,始于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到1983年郭沫若先生主编、胡厚宣先生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图版13册出齐,为一大结穴。《合集》汇总诸家,共收录甲骨41956片, 当时已出材料的主要内容皆已搜罗在内。作为《合集》组成部分的释文及来源表,也将于近期出版。
《合集》以后,又有若干著录问世。其间比较大宗的,发掘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南地甲骨》,收藏品有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与《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甲骨文字》、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和《甲骨续存补编》等等。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正在做《甲骨文合集补遗》的编纂工作。
《合集》及其后种种著录,为全面整理殷墟甲骨准备了条件。例如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等学者安排计划,编著“《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考释类编》(出版时名《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选》等四部著作”,构为“一个完整的系列”〔7〕。这些书籍, 已经取代了多年来人们习用的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等书。其中《甲骨文选》未出,但已有王宇信等主编的《甲骨文精萃选读》、徐谷甫、濮茅左的《商甲骨文选》等,体例略似。
整理工作, 还需要提到香港饶宗颐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8〕。《通检》已出四册,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极便学者。据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甲骨文电脑资料库研究计划”,规模宏大,刻正逐步实施中。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于曾毅公先生1939年的《甲骨叕存》,该书于1950年扩大出版为《甲骨缀合编》。专就抗战前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先生等《殷虚文字缀合》〔9〕、张秉权先生《殷虚文字丙编》〔10〕。70年代,又有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及《甲骨缀合新编补》〔11〕。
据以上叙述可见,甲骨的著录和整理,于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业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今后没有更多工作好做。以材料的搜集而论,国内外还有若干公私收藏,数量尽管不多,仍有精品,令人兴遗珠之叹。著录的方式也可以改进。早期仅用拓本,甚或限于条件,以摹绘代之,不少原物至今已不可见,非常可惜。实则甲骨除文字以外,其本身尚须从许多角度考察研究,不是拓片摹本所能代替。对较重要的标本,采用彩色摄影等等方法著录,将有裨于研究的进展。缀合拼复也有好多工作可以进行。比如《殷虚文字乙编》新版和补遗已出,《甲、乙编》的坑层记录也发表了,使这些发掘材料的进一步拚缀更有条件。
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发端,不知有多少学人于此付出心力。释读文字的作品,在每年出现的甲骨学论作中,总是数居首位。
已出土甲骨到底包含多少不同的字,长期以来学者间有各种估计。多数人根据孙海波《甲骨文编》、金祥恒《续甲骨文编》,推定为5000字以上,然而近日有学者做了仔细研究,指出只有4000字左右,其说当更可据。于省吾先生考释甲骨文字,收获甚巨,其《甲骨文字释林》自序云,甲骨文字“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认识的字中虽有不少属于冷僻不常用者,但在常用字中之不认识者,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说目前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较诸罗(振玉)、王(国维)时代虽然有所发展,但进度有限。”20年前他这番话今天仍旧适用,可见甲骨文的读释是十分困难的。有人宣称在短期内释出多少字,断不可信。
甲骨文的字编,起着汇集文字考释成果的作用。这种字编虽以罗振玉1916年的《殷虚书契待问编》为滥觞,惟其内容限于待考,真正成系统的当以1920年王襄先生《簠室殷契类纂》、1923年商承祚先生《殷虚文字类编》为最早,而最流行的是孙海波《甲骨文编》。《甲骨文编》初版于1934年,1965年出了修订版〔12〕。近年新出的熘惺嫦壬鞅唷都坠俏淖值洹贰?3〕,更为广博精审。结集诸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完备的是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释》〔14〕,近期则有上面谈到的《甲骨文字诂林》,着手考释甲骨文字者都可由之得到帮助。
董作宾先生1935年的名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5〕,是殷墟甲骨分期的开山之作。“断代研究”本为一词,由于大家习引《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古文字学界竟把“断代”当成“分期”的同义语了。甲骨大多是非发掘品,缺少坑位和地层关系的记录,给分期带来障碍。董氏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创立了五期的分期学说,为学者普遍遵循。此后随着殷墟发掘中甲骨新材料的发现,他对自己的分期作了几次补充修改,如在《殷虚文字乙编自序》中提出“文武丁卜辞”之说,在《甲骨学五十年》中认为第一期应包括祖庚。“文武丁卜辞”说引起了一系列讨论,陈梦家先生1951年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虚卜辞综述》)〔16〕,指出“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1953年,日本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两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17〕,也有类似意见。陈梦家等先生的见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据的支持。
在“文武丁卜辞”问题讨论之后,又有“历组卜辞”的问题。历组卜辞基本上即董氏五期中第四期那类卜辞。1928年,加拿大学者明义士作《殷虚卜辞后编序》(未完成),曾认为这类卜辞属武丁后半至祖庚时。1960年以后,我达到类似的看法,1977年以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说后来幸得裘锡圭、林沄等先生的支持发展,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进一步刺激了有关的讨论。由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的检讨,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关于新说的详情,可看1996年末出版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18〕。
甲骨分期讨论持不同见解的各方,对有关研究的深入都有其贡献,这是我多次强调过的。综观讨论的过程,田野发掘的进展实有其决定的影响。最近小屯南地发掘报告的发表〔19〕,使我们对不同意“两系说”的看法有了更多的认识〔20〕。相信殷墟的继续发掘,会促进分期问题的解决,到那个时候,运用甲骨材料去探讨历史文化就将更加便利。
殷墟甲骨的发现,引导到殷墟遗址的确认及其一系列发掘,从而展现出商代丰富光辉的文化面貌,已经载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21〕。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对于我国绵延久远的历史,曾有种种怀疑否定的论点,例如19世纪晚年,有名考古学者德摩根在其《史前人类》中,便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前7、8世纪〔22〕,与其后国内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相合。甲骨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一下子恢复了一大段古史。王国维研究甲骨,论证了商朝先公先王的谱系,他说:“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23〕这在方法论上为古史的重建带来了光明,无怪乎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对王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甲骨学一百年间,名家辈出,论作如林,特别是50年代以来,发展更为迅速。《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出版于1952年,所收876条, 当时已叹为大观,而1991年印行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24〕,竟有16开本631页。繁多丰富的成果,自然不是小文所能缕述的。 好在这些年有了一些概述性的专著,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等。我们期待最近能出现规模更大,像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那样的著作,对20世纪甲骨学作全面的总结。
甲骨学的研究尽管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非常多的成果,但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许多疑难没有解决。实际上,甲骨的奥蕴大部分还不曾抉发,用以探究古代历史文化也大有可为。以为甲骨研究得差不多了的止步自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十几年前,我曾试提过古文字学的15个课题〔25〕,其中5个是甲骨方面的,即卜法和文例的研究、分期的研究、缀合与排谱、历法的研究及地理的研究,今天看来都仍有待探讨。这里想特别说的,是甲骨学今后的发展一定要进一步以考古学为基础。甲骨本身是一种考古遗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甲骨的研究,随着考古学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甲骨的鉴定研究也会引进新的手段〔26〕。相信21世纪的甲骨学将更为发扬光大。
注释:
〔1〕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24~3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第161~164页、30页, 中华书局1983年。同书141页1933 年《通报》苏联布那托夫《甲骨学之新研究》,标题乃后来译文。
〔3〕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载,1930 年周予同先生在《学生杂志》有《关于甲骨学》一文,翌年《开明活页文选》又有周蘧同题文章,两文未见,记此备考。
〔4〕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5〕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0号。
〔6〕孟世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汉字》,《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
〔7〕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序》, 《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参见赵诚《关于〈甲骨文字诂林〉》,《书品》1997年第3期。
〔8〕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甲骨文通检》第一~四册,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1995年。
〔9〕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 科学出版社1955年。
〔10〕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已出6册,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1972年。
〔11〕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年;《甲骨缀合新编补》,同上1976年。
〔12〕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
〔13〕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另有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14〕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15〕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5年。
〔1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7〕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日文),《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18〕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以上叙述参见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李学勤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1995年。 参看郭振禄《小屯南地甲骨综论》,《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20〕李学勤《读〈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待刊。
〔21〕参看丹尼尔《考古学简史》(Glyn Daniel,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logy,Thames and Hudson,1981)第174页。
〔22〕Jacques de Morgan,Prehistoric Man, 转引自〔21 〕第173页。
〔23〕王国维《古史新证》第52~5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24〕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5〕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26〕参看仇士华、蔡莲珍《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5年。
日期:[ 2008-12-01 ] 阅读:3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