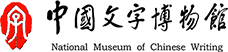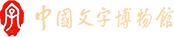“汉字的黎明”再现浙江 首次发掘“刻符玉璧”(图)
核心提示:良渚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此前,良渚文化陶器出现的少量刻画符号和纹饰曾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相关。良渚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此前,良渚文化陶器出现的少量刻画符号和纹饰曾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相关——这一猜想昨天又添佐证,早报记者昨天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获悉,该所日前在杭州市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一件刻有两个符号的刻符大玉璧。这是浙江省境内首次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刻符玉璧”,而这样的“刻符玉璧”目前国内仅4块。对于良渚文化的刻符,一些学者甚至以“汉字的黎明”来作比喻。
浙江首次发掘 “刻符玉璧”
12月13日,杭州市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一件精心打磨得光滑如镜的大玉璧,距今约4000年,其直径为24.6厘米、厚约1.5厘米,属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厚重,圆大,精美。在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仔细辨识后确认,该玉璧上有2处刻符,一处位于玉璧正面,另一处在玉璧内凹边缘。考古专家初步认为,这2个刻符很可能是史前文字符号,相当于后来出现的文字;也可能反映某种宗教信仰,或大型宗教活动场景。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宗教刻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前良渚出土的陶器上发现过不少刻符,但与玉器上的刻符不能比。”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表示,过去在浙江省的良渚正式考古发掘中的玉器从来没有发现过刻符。“因为当时陶器的制作不受限制,陶器上的刻符可能很多是陶工制作时留下的一些记号;而玉器在良渚时期,只有上层贵族、有权势的人才能使用。所以上面的刻符,第一,不是随便谁都能刻;第二,刻上去一定有它的意义。”
据了解,“刻符玉璧”非常稀罕,此前浙江省只从民间收集到一块,一直存放在浙江博物馆。今年10月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开馆,这块“刻符玉璧”被作为该馆镇馆之宝进行展出。“刻符玉璧”直径约为24厘米,正面雕有精细的“鸟立高台”纹饰,表层刻纹浅到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正因如此,展出时还配以放大后的清晰样图。
发现处相当于“良渚时期的上海”
据了解,出土刻符大玉璧的玉架山遗址16号墓位于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在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以东大约20公里处。该古城四面被城墙包围,城墙宽40-60米。城中心是莫角山,学者们认为是良渚时期的中心,住着统治整个良渚文化区域的“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丁品表示,良渚文化辐射整个太湖流域,包括浙北、苏南等地。如果把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看成是一个“国家”,良渚古城就是这一国家的中心,像现在的首都北京。那么发现“刻符玉璧”的玉架山遗址,就是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大城市,可以看成现在的上海。
在该遗址除出土“刻符玉璧”外,还有包括玉冠状器、玉璜、玉镯、玉管串等50余件玉器。其中,以一件高约4厘米、上端宽约8厘米,形如冠帽,造型状若良渚文化“神徽像”上的羽冠的玉冠状器最为珍贵。据了解,玉冠状器一般只见于良渚文化规格较高的大型墓葬中,而且在每一墓中都具有惟一性,每墓最多只有一件玉冠状器出土;只有地位较高的人物才有资格佩戴玉冠状器,而戴着“神冠”的巫师和首领俨然成为神的化身。
此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共发现十多个字。从良渚文化的器物上,能清楚地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反山琮王刻符、余杭南湖陶罐的十一个图文及澄湖良渚陶文、马桥宽把杯图文已经有了文字(图文、刻符、绘画),即在良渚文化的鼎盛时期文字(图文、绘画) 已经形成。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认为,良渚刻画符号都表达了一定的内涵,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在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应当处于从原始记事符号到文字产生之间的过渡阶段,是初期象形文字。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平研究员此前表示,“良渚文化刻符”被认为具有“前文字”的性质,有的刻符近似于装饰性图案,但它们出现在器物的部位和重复程度和可能具有的“语境”与图案有明显区别,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其中必然包括了良渚刻符的加入,良渚刻符应当是汉字间接的祖先。
(2008-12-18)
日期:[ 2008-12-16 ] 阅读:4712